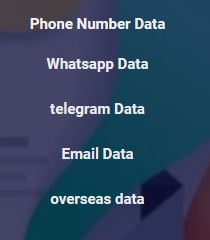显然,法院的起草过程中兼具两种愿景的元素。《规约》何国际法院都必须建立在其成员国同意的基础上这一事实之间实现了微妙的平衡。除其他规定外,《罗马规约》第 27 条和第 98 条也反映了这种平衡。按照传统理解,在上诉分庭对巴希尔案作出裁决之前,这放弃了被告在法院出庭后对官方豁免权的任何要求(如在国家当事方之间),但保留了非当事方在逮捕和引渡程序中可享有的国家豁免权。
无论如何,扩大法院管辖范围的有力工具是赋予它普通属地管辖权。这显然意味着法院将有权管辖第三国国民在成员国领土内的行为。这一点可以通过与侵略罪修正案进行对比来说明。在那里,各方实际上同意对管辖权实行“双 萨尔瓦多 Whatsapp 数据 重锁定”:犯罪行为需要同时发生在缔约国领土上和由缔约国国民实施。毫无疑问,在最大限度扩大法院管辖范围方面,没有对法院根据第 12 条的普通管辖权这样做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件好事。尽管如此,在孟加拉国/缅甸案之前,第 12 条也可以涵盖跨境犯罪这一点并不明显。
然而,授予法院哪怕是“普通”的领土管辖权是否是一个错误?我曾预测,法院第三位检察官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将是管理可能难以解决且无止境的调查,调查对象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缅甸、俄罗斯/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乌克兰以及(也许)巴勒斯坦/以色列等局势中的非国家当事方的行为。将中国添加到这个名单中似乎并不可取。问题很简单:除了一人认罪外,法院仅成功起诉了刚果民主共和国中级叛军军阀的罪行。针对肯尼亚或科特迪瓦等成员国国家元首的案件已不复存在。法院成功起诉那些本身没有义务协助法院的国家高级官员的前景似乎有限。此外,如果这一通讯得到传播,我们将面临一个有趣的境地:所有三个未加入《罗马规约》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都将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审查。
尽管如此,孟加拉国/缅甸案打开了一扇可能很难关闭的司法管辖权之门。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这并非不可避免。有一种在法律上看似合理(但远非令人信服)的论点,即法院的属地管辖权应理解为主观管辖权。这种要求,即犯罪必须在缔约国领土上开始,才属于管辖范围,仍然适用于阿富汗(以及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情况。尽管如此,它将限制客观属地管辖权原则的影响,使其无法将法院的管辖范围扩大到非缔约国国民在缔约国领土之外发起的犯罪。
- Board index
- All times are UTC
- Delete cookies
- Contact us